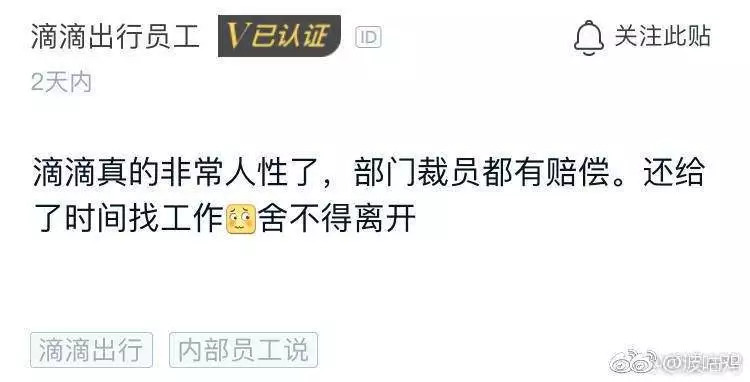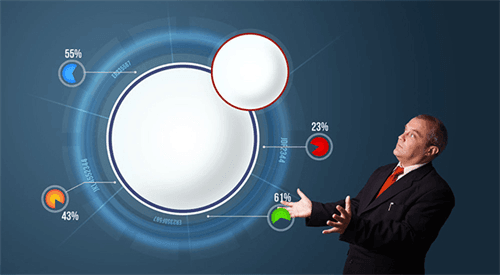郝思佳永远也忘不了去年8月25日的那个上午,一则乐清女孩在乘坐滴滴顺风车时惨遭司机杀害的新闻让她感到震惊。
在三个月前,滴滴顺风车部门曾因为另一起乘客遇害案件,李茹所在的技术部负责下线了计划中的营销活动,弱化处理了与社交相关的页面,同时将与第三方的合作全部暂停。
这些页面和活动尚未重新上线,滴滴顺风车便遭遇了第二次“轰炸”, 负责运营相关工作的郝思佳觉得有点懵。
当时,所有舆论将矛头指向滴滴顺风车,客服的响应速度、重大问题处理流程、平台的审核成为被外界指责的焦点。甚至时任顺风车负责人黄洁莉曾对顺风车的描述“sexy”(实际语境下等同于“cool”)也被误认为是具有某种特别的引申含义。
还没缓过神,郝思佳就被紧急召回到工作岗位。
当天,她和同事与产品经理直接碰了个头,便迅速下线和停掉了顺风车的所有营销活动,同时也撤下了滴滴App中顺风车的推广弹窗。
为了改变局面和强化安全,滴滴随后做了一系列整改:
上线人脸识别、录音等功能、添加紧急联系人、行程一键分享、暂停深夜时间段叫车服务、加大自建客服团队规模、以及完全下线顺风车业务……
在过去几年带领滴滴一路高歌猛进的程维则直接在公开信中直白承认公司的错误,“好胜心盖过了初心,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内部体系提升跟不上规模扩张,就像灵魂跟不上脚步。”
去年国庆节,程维、柳青、陈汀、朱景士等管理团队穿着文化衫,跑到五彩城购物中心,拿着调查问卷记下了不少用户的意见和建议——正处于安全整改期的滴滴,急需摸索出一套可行的安全标准。
在线上,滴滴还做了一个“公众评议会”,就一些争议较大的话题面向用户征集意见,比如“司机是否有权拒载独自醉酒的乘客”、 “乘车过程中,车内属于乘客私人空间或是公共环境”、“全程录音功能是否侵犯司乘的个人隐私”等等,并公开了平台上真实的案例,向公众展示了出行的复杂难题。滴滴希望平台的决定不是“拍脑袋”出来的,而是在征求过民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在滴滴顺风车下线的这段时间里,相关负责人不得不向基层员工做一些口头承诺,然而高层决策并未到内部团队传达的阶段,他们更多能做的只是安抚。
腾讯《深网》了解到,自乐清事件发生后,顺风车的员工们听到过多次“业务很快上线”的说法。一开始,他们还对此坚信不疑,但迟迟不来的上线通知,让他们觉得,比起“直接砍掉”,那种模糊、未提供任何明确事实的说法更让人心神不宁。
对于部分顺风车员工而言,虽然和滴滴一起承受着巨大压力,但不愿相信此前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白纸。这个产品承载了他们的理想和付出,他们渴望有机会再次证明自己。
张莉是滴滴顺风车的老员工,从2015年就在顺风车团队,见证了顺风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最辉煌的高光时刻,也在去年因为安全事件,和顺风车一起进入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
外界的许多评论和谩骂,张莉有时候看多了心里很难受,心情低落的时候,她会去微博上找一些用户希望顺风车早日上线的留言来给自己打气。“滴滴有自己的错,但顺风车作为一个每天服务几百万人的产品,在过去三年创造的社会价值不应被彻底否定。”张莉告诉《深网》,让顺风车消失对于那些真正需要顺风车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滴滴的2018年无疑是艰难的,除了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的常年亏损也让其不得不收缩编制和人力成本。
顺风车部门也压力陡增。
36氪曾报道,一份滴滴出行内部流传出来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2018年持续巨额亏损,全年亏损高达109亿元人民币。同时,2018年全年滴滴在司机补贴方面投入共计113亿元。
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年终奖减半。李茹和孟严告诉腾讯《深网》,顺风车部门员工的年终奖更少。
一些原本认同并坚信滴滴顺风车可以大放异彩的员工内心逐渐松动,在到达梦想彼岸之前,他们必须考虑更加现实的生存问题。趁着工作节奏还算宽松,一些人开始悄悄去外部面试新的岗位。他们希望在最坏的结果来临之前尽量多做一些准备。
众多出行业务中,顺风车是名副其实的“共享出行”,它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
李茹加入滴滴顺风车时,正是因为看好这一模式才让她做出的最终决定。而现在,上线未果的顺风车让她的职业计划被打乱,李茹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新的规划。
关于顺风车为什么迟迟不上线,张莉也有自己的想法,她认为虽然顺风车是滴滴自己下线的,但随之而来的十部委入驻式检查,已经将问题提升到了监管部门的高度。在检查组公布的27条整改要求中,直接定性顺风车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要求在完成整改,确保安全之前不得上线。
“如果要再上线,产品要怎么改,安全要怎么做,才能让主管部门和公众认可,确实挺难的。”





 手机版
手机版 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